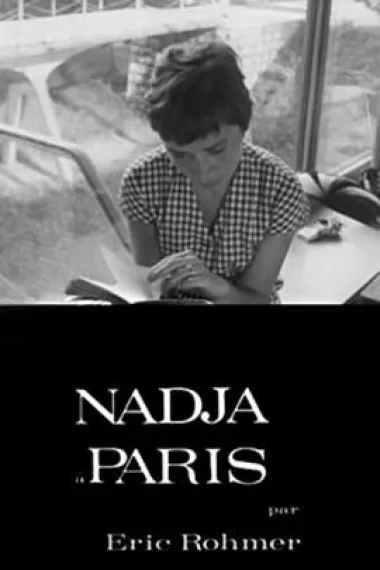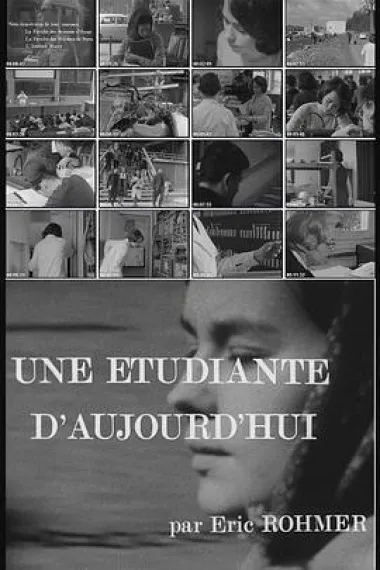埃里克·侯麦 (1920) Eric Rohmer
埃里克·侯麦的“难以言喻”一直令其仰慕者难以阐释。
这种挑战部分源于:尽管他身处法国新浪潮运动之中,其作品却与同侪大相径庭。这或许源于这位导演不愿随波逐流的个性,但也有观点颇具说服力地指出,事实上他比同代人更忠于这场运动的原始精神。此外,情节并非他的首要关切。对侯麦而言,角色的思想与情感才是核心;正如人的自我状态难以界定,他作品的内在生命也同样难以捉摸。因此,影迷们很少用具体词汇描述,而更常使用“精妙”、“机智”、“美妙”和“神秘”这类修饰语。在昆汀·塔伦蒂诺与丹尼斯·霍珀的一次访谈中,他道出了几乎所有爱好者的心声:“你得先看一部[他的电影],如果你有点喜欢那部,就该看看他其他的作品,但你必须先看一部才能知道自己是否喜欢。”
批评者则毫不掩饰他们的不满。他们用“像课堂剧一样乏味”、“矫揉造作又令人疲惫”和“学究式的喋喋不休”这样的词句来形容。吉恩·哈克曼在1975年的《夜行客》中饰演了厌倦一切的侦探哈里·莫斯比,说出一句如今已成经典、概括了这些感受的台词:“我看过一部侯麦的电影。感觉就像看着油漆变干。”无可否认,极度缓慢的节奏以及冷漠、自我沉浸的角色是他的标志;有时,甚至他最忠实的支持者也会就此发表尖锐评论。评论家宝琳·凯尔曾说:“悲喜剧式的琐碎已成为侯麦的专长。如果他不再像对着节拍器一样执导,他的情感会更容易接受。”侯麦的支持者甚至会引用对他的攻击——在导演中,他可能确实是独一份。他们陶醉于他的电影中“无事发生”的特质,沉迷于那些密集的高雅对话块,也乐于见他美学风格的一以贯之。然而最重要的是,他们被这位导演的真诚所打动:他毫不妥协地袒露人类灵魂与“生活本身”。
埃里克·侯麦是谁?他于1920年12月1日出生在洛林小城南锡,本名让-马里·莫里斯·舍雷尔,后移居巴黎,成为一名文学教师和报社记者。1946年,他以笔名吉尔伯特·科尔迪耶出版了他唯一的小说《伊丽莎白》。不久,他的兴趣转向评论,并开始频繁出入由档案管理员亨利·朗格卢瓦创办的法国电影资料馆,在那里结识了即将成为新浪潮旗手的让-吕克·戈达尔、雅克·里维特、克洛德·夏布洛尔和弗朗索瓦·特吕弗。也是在这时,他采用了笔名“埃里克·侯麦”,融合了演员/导演埃里希·冯·施特罗海姆和小说家萨克斯·侯麦(傅满洲系列作者)的名字。他的首部电影《流氓日记》拍摄于1950年,同年他与戈达尔、里维特共同创办了《电影公报》。次年,侯麦加入安德烈·巴赞主持的《电影手册》,并于1956年至1963年担任主编。作为一本极具影响力的刊物,《电影手册》不仅为他提供了宣扬新浪潮理念的平台,也让他得以提出关于好莱坞的修正主义观点。后者的一例是他与夏布洛尔合著的《希区柯克:前四十四部电影》,该书以高度赞誉的笔触探讨了阿尔弗雷德·希区柯克。
侯麦早期的导演尝试成果有限。至1958年,他完成了五部短片,但其唯一的长片尝试——改编自塞居尔伯爵夫人的《模范小女孩》——未能完成。1962年的《狮子星座》是他的长片处女作,但直到十年后他才获得广泛认可。在此期间,他完成了十一部作品,包括其“六个道德故事”系列中的三部。这些电影致力于审视人们在诱惑阵痛中的内心状态。《蒙索的女面包师》和《苏珊的生涯》是平淡的黑白片,最好地充当了他后期作品的蓝图。它们也标志着他与巴比特·施罗德商业合作的开始,后者出演了前一部影片。《收集男人的女人》是他首部重要的彩色电影,曾被误读为一部“洛丽塔”式电影;在更深层面,它质疑了人们收集或拒绝经历的方式。侯麦的第一个“成功之作”是《慕德家的一夜》,该片获得两项奥斯卡提名并赢得多个国际奖项,至今仍是他最知名的作品。片中,叙述者在向未来妻子弗朗索瓦丝表白爱意的前夕,与一位名叫慕德的美丽离婚女性共度一夜。两人与一位朋友一起,讨论了生活、宗教和帕斯卡的赌注。当与性感的慕德独处时,叙述者被迫考验自己的原则。该系列的最后两部,《克莱尔的膝盖》和《午后之爱》,是中年危机故事,巧妙地重申了自我克制是通往救赎之路的理念。
侯麦的第二个系列“喜剧与箴言”探讨欺骗。《飞行员的妻子》讲述了一个天真的学生怀疑女友不忠的故事。通过跟踪她的前男友并最终与她当面对质,我们发现了他在不同层面上欺骗自己的程度。另一部杰作是《沙滩上的宝莲》,一部关于青少年成长及其成年监护人幼稚滑稽行为的海滨电影。在该系列其余作品中,《绿光》和《我女朋友的男朋友》最引人入胜。导演的最后一个系列是“四季故事”,同样呈现了古怪人物失调的关系。不过,与“喜剧与箴言”的社会游戏不同,这个系列探索的是情感孤立者的生活。《春天的故事》和《冬天的故事》更具创意,后者重温了《慕德家的一夜》中的“赌注”主题。正如他的作品在主题上自我呼应,侯麦也让演员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反复出现在他的电影中。最后一部《秋天的故事》集结了他最喜爱的女演员玛丽·里维埃和贝阿特丽丝·罗曼,与《冬天的故事》一样,它回顾了之前的作品《好姻缘》,审视了罗曼德寻找丈夫的追求。
自1976年起,侯麦还制作了各种非系列作品。《双姝奇遇》和《巴黎的约会》均由短片组成,是带有讽刺意味的道德剧,不太值得关注。与之对比,华丽的古装剧《O侯爵夫人》出色地研究了18世纪贵族荒谬的礼节规范,并获得了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。遗憾的是,他的其他时代剧未能取得同等成功。《帕西法尔》虽具原创性,却是一次舞台化亚瑟王故事讲述的失败实验;而精美却沉闷的《贵妇与公爵》同样无法满足其大多数影迷的期待。尽管如此,这位导演展现了惊人的连贯性,能在职业生涯如此晚期交出这般水准的作品,令人惊叹。他留给我们的遗产可与任何电影作者媲美,过去四十年间 arguably 有多达十部力作。那么,为何他在新浪潮乃至所有电影天才中获得的荣誉最少?
关于侯麦独特癖好的故事比比皆是。作为一名热心的环保主义者,他从未开过车,也拒绝乘坐出租车。他家中没有电话。他曾将《慕德家的一夜》的制作推迟一年,坚持某些场景只能在圣诞夜拍摄。有一次,他要求配乐的音量调到观众听不见的程度。他自称“商业”,但他的电影在艺术院线放映利润微薄。通常,这类轶事会拉近他与知音的距离。然而,他最显露本色的一点是,他拒绝采访并回避聚光灯。例如,希区柯克总是乐于谈论本行,而侯麦则让他的电影自己说话。他并不担心人们如何看待它们,而是关心人们确实在思考它们。
试图用言语取代前述的“难以言喻”是危险的。在不祛魅侯麦电影的前提下,仍有一些广泛的品质可被指出。首先,它以哲学和艺术的完整性为标志。早在克日什托夫·基耶斯洛夫斯基之前,侯麦就提出了电影系列的概念,这使他能以独特的方式在自己的作品基础上构建。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,他对抵抗诱惑感兴趣,作品中未发生之事与已发生之事同样引人入胜。与他的灵性相关的是他对命运与自由意志相互作用的着迷。某种选择始终是他故事的核心。然而,尽管他的叙事缺乏传统的戏剧性事件,他却表现出对近乎超自然的巧合的偏爱。为了保持逼真性,他比同时代人更多地使用“长镜头”以及更简单、更自然的剪辑过程。他很少使用音乐和音效,而是专注于人声。在这些声音中,虽然叙述者通常是男性,但我们表面上接触的是他们的主观体验,而他影片中的女性角色比男性更聪明、更复杂。最后,尽管侯麦的作品充满深思,却很少给出定论。它令人耳目一新地非好莱坞化,非但没有提供逃避现实的途径,反而迫使我们直面我们所生活的世界。